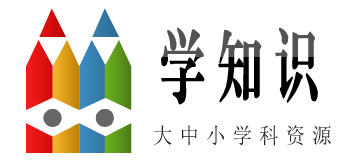文 / 商洪旺

(一)心尖上的“石猴桥”
我的家乡有条古老的河,滹沱河,它悠悠地流过镇子千百年;滹沱河上有座古老的桥,登瀛桥,它静静地横卧在那里几百年。
我家乡的人,并不称它“登瀛桥”;因为坐落在杜林镇,只是有的外乡人便称呼它“杜林石桥”。可我们当地的人们,无论老幼,都习以为常地称它“石猴桥”。因为就在桥的东首栏杆上,蹲踞着一只神态肃然、双目凝望的石猴。几百年,东来西往的人们,总是要忍不住轻抚一下它的头,还有它的背。它早已变得光滑油亮,愈加地神态生动起来,更加惟妙惟肖地像一只真的小猴,踞坐在栏杆上,打量着每一位过桥人呢。
不知道从何时,这只石猴仿佛有了灵性;更不知从何时,我的家乡便增添了一项习俗,每年正月十六的晚上,男女老少遛百病,都要走上石桥,摸一摸石猴。一边摸一边念叨着:“摸摸石猴头,好运正当头;摸摸石猴背,好运跟一辈;摸摸石猴脚,好运少不了。”

从此,人们便忘掉了这座桥原本的名字;从此,它却拥有了一个虽说很俗,但是更接地气的,更能承载我家乡人一种情怀的“小名儿”——石猴桥。
几百年,无论风雨变迁,无论沧海桑田,它岿然不忘它的使命,连接着镇子便利的交通;几百年,无论盛衰兴替,无论得失荣辱,它依然激荡它的情怀,凝聚着家乡人那份厚重的爱;而今,它俨然化作成一个地标,这地标已经稳稳地、深深地坐落在每一位远离故土、怀念家乡的人,他们的心尖儿上。

(二)桥头有家包子铺
每逢农历的二和七,便是镇子赶集的日子,也是镇子上最热闹的时候。四邻八乡的人们,一下子就涌进镇子的街道。卖的买的,走的瞧的,叫喊的闲逛的,提篮的背筐的,熙熙攘攘,人声鼎沸,像开了锅一样。
集市纵贯镇子东西,而集市的中心,就在一处十字交叉的街口,人们都习惯地叫这“十字街”;十字街向东百十步,便是石猴桥。桥上更加热闹得很,挤满了小商小贩,和西去东往的人,常常是摩肩接踵,小孩子们被夹在大人们的腿间,哭着喊着闹着,很无助地跟着大人缓缓地移动。走过了桥,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。
紧挨着桥头北,临着西河沿一小间低矮的铺子,竖着杆子,挑着一只风吹日晒的招子,倒还清晰地在上面写着“包子铺”。爷爷说,这儿很早就有这家包子铺呢。是不是打有了这座石猴桥,走卒贩夫,商旅往来,为的打尖歇脚?不得而知。
这个铺子还在,还是桥头北,河沿西;还是一间低矮的小房子,只是岁月的烟熏火燎,更加地有了年代感;招子没有了,更现代的电喇叭也不用,省得吵闹得大街乱哄哄的,一点安宁都没有。

其实,不用招牌,一早一午间飘来的味道,这几十年不变的味儿,便是他家的招牌。变化的,是四十多年前,五分一个,一角俩,变成了现今一元一个了。
小时候买上两个,用纸包好,托在手心上,三口两口地吃掉,不管烫不烫,为解馋。如今,花上两元,用白白的食品袋盛了,手指勾着袋子,并不急于吃掉的。我想,大概是为着某样情怀,一种心心念念,永怀难忘的情怀。
离开家乡久了,仿佛故乡的一切都要生成一种味道,而这味道又常常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一个人慢慢咀嚼,甚至和着苦涩的泪水。
踱到桥上,一手凭栏,眺望着远方。桥下滹沱河的水,清浅而明亮,静静倒映着两岸高高低低的人家。忽然,这情怀就像那熟悉的味道,顺着滹沱河开阔而辽远的河道,越飘越远……

(三)老宋.小宋
下桥,拐过包子铺,只隔一间小小的修表店,便是老宋师傅的理发店。
老宋师傅其实并不老,也不是本地人,他说话的腔调儿,听起来怪怪的。但老宋师傅为人很是和蔼,不管老幼,进得理发店的门儿,都是用他那怪怪的口音,笑着抢先一步地说,“快坐、快坐。”其实他的店里只一张条椅,能坐仨人就挤满了;靠窗一张小床铺,也能坐上四五个;常常晚来的人,并无处可坐的。虽然说着话,他却并不停下手中的活儿。
老宋师傅,总被很多更老些的人称“小宋”,连师傅俩字也不带的。原来,宋师傅打十几岁,该是半大小子的时候,就在这学徒,后来独自撑下门面,自己成了师傅。这“小宋、小宋”的,就被人一直叫到现在,尽管我看他已经有些岁数了,只是进门来的,都是老主顾,他们会比老宋师傅,看起来要更老得多。

老宋师傅个头不高,身材瘦削,却显得很飒利,手艺也好。他那手艺,绝对是了得。一把推子,一把梳子,在你的头上,上下翻飞,不大一会儿的功夫,你所想要的发型,便呈现在镜子中。
那些老主顾们,大多是来剃头的,这是老宋师傅最拿手的。一把剃头刀,在板带上勒得铮亮。打湿的头皮在剃刀下,发出刷刷的声响。也就半袋烟,一个铮亮的光头,暴露着青色的头皮,闪闪发光。
接着,老宋师傅问都不问,脚下一蹬,那重笨的铁椅子,便放平。重新围好围裙,早就热好的毛巾,叠成长长的一条,敷在下巴上。片刻,揭开毛巾,一把毛刷蘸着肥皂水,在下巴、嘴唇、鬓角,刷刷几下,便泛起白白的泡沫。剃刀剃上几刀,老宋师傅便抄起板带,再勒上它几下,又是刷刷剃上几刀;再勒几下,再剃几刀。反反复复之后,还要捏起嘴唇来两刀,额头两刀,鼻子两侧各一刀。从鼻尖到额头一刀,额头再左右两刀。脚下一蹬,笨重的铁椅子立起,扯去围裙,这老主顾站起身,对着镜子,左看看,右瞧瞧,大手在下巴上重重地摸上一把,再搓上一把布满皱纹、饱经沧桑似的脸,然后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。老宋师傅一旁看着,笑眯眯的,不知是为自己的手艺,还是为着老主顾。
我倒想起来庖丁解牛,游刃有余,踌躇满志,不过宋师傅这样吧。
最绝的,宋师傅随手向后一甩,看都不看,那蘸着肥皂水的毛刷,不偏不倚,“啪”地一声,正好落在水盆里。这一甩,很多年都惊艳着我。
那时盼着快快长大,也好如此,躺在那笨重的铁椅子里,等着老宋师傅,敷毛巾,打泡沫,剃胡须,提提唇,净净脸。也听他不用回头便“啪”地甩走毛刷。最后再敷一敷热毛巾,然后对着镜子,摸摸下巴,搓搓脸,也一样志得意满地,走上石桥,迎着河道飒爽的风,静享当下的闲适与安逸。
当胡子茬儿满了下巴,却是更小的小宋,他的手艺不差着老宋师傅,让我一样享受到那份手艺带给的满足感,只是我却平添了一份怀想,和淡淡的忧伤。

(四)老沈家的羊肠子
修表店的对过儿,每到赶集的日子,有个肩挑的小吃摊儿。一头儿是个火炉子,炉子上架着一口锅,锅不大,是四出沿儿的,便于放些碗筷。一头儿是个木架,放着食材和家伙什。
尺把长的刀,从翻滚的锅里,挑起食客想要的,搁在碗里,一手提着,长刀贴着碗边,快速地削切着。满满的一碗,过上几遍汤,然后端给食客。
食客们或站、或蹲,或靠着墙根儿,也有就着木架的。大多自带的窝头,也有油条,极少。一口窝头,一口连汤带肉的,吃得热火朝天,大快朵颐,个个好像都甩开了腮帮子。
这便是,从镇子乃至响遍整个沧州的名吃——羊肠子,沈家羊肠子。

一角钱可以切一碗,两角钱能一大碗。一角钱的血肠、肥肠和油碎儿,两角钱的再加苦肠、羊拐子和羊房子,那时羊宝、羊鞭,不值钱,不像现在贵得很,那时想吃的就给切上几刀。
要一角钱的血肠、油碎儿,和几刀苦肠、羊房子,虽不是满满的一碗,也让那个苦巴苦紧年代的我,美美饱餐一顿,况且又不是每个集都能赶巧的。
这一喝,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喝到青年,喝到成年,又喝到如今。从镇子喝到城里,从城里喝到省里,从省里又喝到省外。爱屋及乌,从羊肠子喝到羊杂汤,从羊杂汤喝到羊肉汤,又从羊肉汤喝到全羊汤。
喝着喝着,日子就不再为裹腹而计较,却对味道越来越挑剔。鲜美虽说是追求的极致,可鲜美的东西只是愉悦了齿颊而已。
当味道和记忆叠加在一起,吃喝便是生长于内心并固化的一样情怀。

沈家羊肠子是,王家包子、沙家烧饼、李家大车店的焖饼烩饼也是,而这只要稍稍远离了故土那么一点点,这情怀就会浓浓地熏染你的每一时,每一刻。无论走到哪里,总也忘不掉那记忆中的味道。就像这石猴桥,连接着的不再是滹沱河两岸的交通,而是远行人和家乡的剪不断的情丝,让人忘不掉我是故乡人,我从故乡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