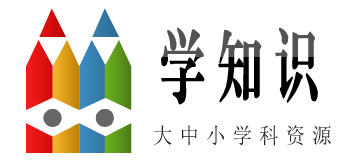父亲从沙漠寄来了一副防风镜。
从我记事开始,它就被父亲带在身上,天长日久,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。这副防风镜常高高地架在父亲的额头上,漆黑的镜片布满了划痕,镜片周围的橡胶也日渐松弛且褪色泛白。这让我想到了父亲那常年受风沙洗礼的苍老的手背,他和他的防风镜都衰老得太快了。
我已经用不上它了。我的窗外吹来上海潮湿的风,这是沙漠之外的世界,有海,更有灯火璀璨高耸入云的大楼。我如同一个闯入者,被沙漠打磨得有些笨拙,在校园,在街头,处处显得格格不入。我在电话里压抑着抽泣声向父亲倾诉,于是他给我寄来了这副旧防风镜。
父亲是沙漠里的小学教师,扎根在那片漫无边际的黄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他第一次走进课堂,问学生:“沙漠外面是什么?”学生的回答无一例外都是“沙漠”。或许是那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让他想起了自己在上海见过的孩子,他决定留下来,让那些生在黄沙深处的孩子有朝一日可以望见高山、草原、大海,望见更广阔的天地。去学校的路上要戴防风镜,可即使戴上,狂风卷着厚重的尘沙而来时,人依旧寸步难行。那天父亲迟到了,但教室里的孩子无一缺席,都端正地坐着等他。
那之后,父亲开始戴着他的防风镜种树。
我在沙漠中出生,在父亲的教室里长大,听着他讲那些关于沙漠之外的故事。看着在乡亲们的努力下越发青翠的家乡,我一步步走出沙漠,走到上海。父亲的背驼了,防风镜旧了,一届届学生虽仍然回答着“沙漠外面是沙漠”,却也有不少学生走向外面的世界。
每一次,父亲都告诉他们:沙漠外面是海,是信念凝成的海,是充满希望的海。他们有的又回到了沙漠,做着和父亲同样的努力。我曾担心自己会在习惯了城市的舒适之后难以割舍现有的生活,这副防风镜打消了我的顾虑。
我像小时候那样戴上父亲的防风镜,望向窗外奔流的黄浦江。我的目光溯流而上,穿过高楼与灯火,拐进沙漠深处那座小小的城,落进教室,落在三尺讲台与父亲的盛年容颜上。我会记得我从哪里来,我会像那干旱沙漠中顽强生长的红柳一样,扎根在那处生我养我的沙漠里,用自己的枝条遮蔽一片风沙,投下一方阴凉。